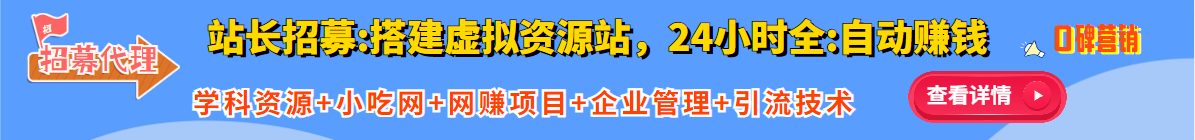小象科学小学一二年级科学同步课 (含上下2个学期)
课程目录:
246[完结] 科学课同步学一二年级上
-01.采集和观察植物.ts 38.82M
02.观察植物的叶片.ts 28.62M
03.画一片叶子吧.ts 23.18M
04.种一棵植物吧.ts 27.41M
05.植物是“活”的吗? ts 37.35M
06.观察和认识身边的植物.ts 30.92M
07.认识花朵.ts 18.21M
08.认识果实.ts 21.13M
09.认识餐桌上的植物.ts 15.72M
-10.日常生活中的植物.ts 19.50M
-11.植物的最强能力.ts 37.98M
12.认识动物.ts 20.73M
-13.水果腐烂的秘密.ts 27.02M
14.在观察中比较.ts 17.88M
15.起点和终点.ts 22.75M
16.用手来测量.ts 15.75M
-17.橡皮也能做尺子.ts 27.83M
-18.自己动手做尺子! ts 35.61M
19.最终的公平排名.ts 26.53M
-20.如何被眼睛欺骗.ts 22.89M
-21.跳远大赛.ts 31.88M
22.用身体去测量.ts 39.82M
23.简易的身体骨架.ts 20.82M
24.重量怎么测量呢? .ts 30.97M
25.温度怎么测量呢? ts 18.7BM
247[完结] 科学课同步学一二年级下
01.发现物体的特征.ts 40.23M
02.谁轻谁重.ts 51.74M
03.认识物体的形状.ts 37.39M
-04.给物体分类.ts 34.56M
05.观察一瓶水.ts 42.5BM
06.它们去哪里了.ts38.82
07.认识一袋空气.ts 43.33M
08.我们知道的动物.ts 47.46M
-09.校园里的动物.ts 29.26M
10.观察一种动物.ts 43.03M
11.给动物建一个"家”.ts 42.50M
12.观察鱼.ts 35.83M
13.给动物分类.ts 32.23M